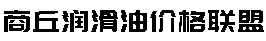孔子“晚而喜《易》”新论
(常会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研究部,100007)
【摘要】孔子的性命天道思想是与孔子习《易》分不开的,《论语》中孔子“罕言性命天道”是与孔子习《易》时间甚晚密切相关的。由于孔子习《易》以至好《易》的时间甚晚,据朱子分析可能近七十岁,所以诸弟子们很少听到孔子关于“性命天道”的论述。如果孔子习易在晚年得以成立的话,那么《论语》中的一些章节,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认识。而结合《论语》、《礼记·缁衣》、郭店简《缁衣》、马王堆帛书《要》篇等,我们可以知晓,孔子其实并不排斥占筮,甚至在晚年经常占筮的。孔子是将德义放在最前,而将占筮放在后面的,占筮之目的,亦在于观德义之不爽。这就与同时代的所谓巫史有了根本的不同。
【关键词】 孔子 晚而喜易 性命天道
关于孔子“晚而喜易”,历来有所争议。孔子对于《易经》的态度,在历史上也是扑朔迷离。那么,孔子的“晚而喜易”,是说孔子晚年才喜欢上易经,才开始真正研究易经呢?还是孔子早年就已经开始研究《易经》,只是到晚年更加热爱《易经》?如果是前者,那么孔子习《易》的时间应该较晚,那么他关于《易》的一些言谈在早期和晚期应该是有所差异的。相反,如果是后者,那么孔子对《易》之态度应该是连贯一致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有《论语》、《史记》、马王堆帛书《要》诸篇等等,特别是马王堆帛书《要》诸篇,更是给我们提供了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由于有了马王堆帛书《要》诸篇,民国年间诸多著名易学大家的观点可以得到进一步矫正。对于孔子学《易》的历史疑团,我们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孔子晚而喜易的论述,历朝历代诸多学者例如司马迁、朱熹、刘宝楠等也都阐述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结合以上诸多历史资料,对孔子“晚而喜易”这一历史史实有一个更为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一、《论语》之“性命天道”与孔子“晚而喜易”
笔者在研究《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关于“性命天道”的认识和看法时,发现两者对于“性命天道”之认识和理解是不一样的,又加上刘宝楠《论语正义》之注解,我们似乎可以隐约认识到《论语》之“性命天道”与孔子“晚而喜易”似乎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在《论语》中,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子贡在这里言孔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至于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那么这里的“文章”以及“性与天道”指的是什么呢?参《论语集解》:
章,明也。文彩形质著见,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
再参看《论语集注》:
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
《集解》与《集注》对“文章”注解相近,而对“性”“天道”理解则相异。《集解》以为“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集注》则认为“性者,人所受之天理”,性为人所禀受是相同的,但一曰“受之以生”,从后面其引《易传》之言,可知此是言受之于天地(或乾坤,因易以乾坤或天地为本),一曰“受之以天理”,即《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此是宋儒之专用,亦是其思想体系之顶端。《集解》之天道,盖汉魏之际所解天道,受《易》影响,故解为“元亨日新之道”。而程朱理学则以理、天理来解天道,从理学本体论上来予以理解,故与《集解》相异。另对于“不可得而闻”,两者理解也不相同。《集解》认为性与天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而《集注》则认为性与天道,是夫子所罕言,故学者不得闻。同时,朱子认为孔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此始闻之,而谈其美,则程朱在此是认为子贡闻听了夫子的性与天道之论。
刘宝楠《论语正义》又曰:
“天道,元亨日新之道”者,元,始也。亨,通也。《易•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此“元”为始也。通则运行不穷,故日月往来以成昼夜,寒暑往来以成四时也。乾有四德,元亨利贞。此不言“利贞”者,略也。天道不已,故有日新之象。性与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语上,故不可得闻。其后子思作《中庸》,以性为天命,以天道为至诚。孟子私淑诸人,谓人性皆善,谓尽心则能知性,知性则能知天,皆夫子性与天道之言,得闻所未闻者也。
由此来看,刘宝楠亦以为天道即元亨日新之道,即《易》所言乾之四德。而文章在刘氏那里解释为“诗书礼乐”,我以为深得其旨。因为古代之文非如现代之文,特别在《论语》中指的是古代典籍,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等。而孔子所教的古代典籍,又恰恰是其所整理的“诗书礼乐”,所谓“六经”。又《易》为孔子晚年所极喜书,读《易》曾“韦编三绝”。据《史记》所载,得其传者仅子夏、商瞿(晚年弟子)而已。诚如此,则孔子罕言性与天道明矣。而朱子之《论语集注》与刘宝楠之《论语正义》后面提及子贡应是闻夫子“性与天道”之言,亦可说明子贡的确是听到过的,不然又如何发此语。此外,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
《论语集解》:罕者,希也。利者,义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论语集注》:罕,少也。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论语集解》认为:利者,义之和也。此注解采自《易传·文言传》:“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而《集注》则认为计利则害义,一个将义与利结合起来,一个则将义与利截然对立。也即在《集解》那里,义与利是可以相容的,而在《集注》那里,义与利是水火不相容的。又《集解》:仁者,行之盛也。这里是以行解仁,将仁更多作为一种外在的功业。而《集注》程子则认为“仁之道大”,很明显,程子在这里还是将仁作为一种天道或者义理来看待的。
那么何者解释为上呢?结合《论语》相关章节,我们会看到孔子所言“利”11处,更多与小人、与利益结合而言,则《集注》所言应为上。命,《论语》中提及24处,多半言天命。仁,《论语》中提及109处,皆言“仁德”或“仁德之人”。刘宝楠以此数量多少来解三者先后次序。同时他又曰:“夫子晚始得《易》,《易》多言‘利’,而赞《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下,不可语上,故弟子于《易》独无问答之辞。今《论语》夫子言‘仁’甚多,则又群弟子记载之力,凡言‘仁’皆详书之,故未觉其罕言尔。”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依照此章,孔子学《易》似在五十前后。但参朱子《论语集注》:
刘聘君见元城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卒。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记作为“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学,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
对于朱子之引论,一则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加”与“五十”,尚有“假”与“卒”之争论,但朱子得出的孔子此时习易已几七十无疑是有道理的。如果再参照新出竹简帛书如马王堆帛书《要》篇来看的话,其言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我们可以断定孔子习《易》应甚晚,其上限应下移。《汉书•儒林传》云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又《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上面朱子《论语集注》言孔子当时年已几七十,非如邢昺《论语注疏》所言四十七,则其传《易》于门人弟子又更晚矣。总之,孔子罕言“性命天道”若从孔子“晚而喜《易》”入手,似能解通,有马王堆帛书《要》篇、朱子《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以为论证。
又: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
由此可知,孔子认为君子应该知命。但此章已在《论语》全书之最末,可知其应是孔子晚年所言,或曰其晚年研《易》之后所言,亦能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章作一论证。
如果孔子习易在晚年(如几七十)得以成立的话,那么《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历来有争议的话也是可以解释通的。按照朱子的注解,又据《史记》,我们可以认识到,古代“加”“假”似乎相通。但是,“五十”是否就是“卒”这颇值得商榷,毕竟两者差异还是较大的。如果我们从孔子晚而习易入手来分析,那么以上孔子这句话可以认为是孔子晚年之言,是说孔子在晚年习易大有受用之后,感慨说假如再多给我数年,五十岁的时候学《易》,那么就可以没有什么大过了。这样是可以解释通的,而且清儒刘宝楠亦是持此观点的。孔子言性命天道之言很少,似乎也是因其晚年习《易》所致,所以在《论语》中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又“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
二、孔子“不占而已矣”再论
在当前国学热兴起,让人为之雀跃的同时,我们看到市场上还充斥着“算卦”、“算命”这样的客观情况,其中不乏以此骗财谋利者在。如何认识这些伴随着《易经》这一古老的经书而来的这些现象,是摆在学者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要想认清这类现象,就必须回归易学本身,对易学进行重新学习和反省。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关于占筮,即便是现在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纳甲筮法、梅花易数、铁板神数、奇门遁甲等等。而在先秦时期,则有夏朝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坤乾》)、周代的《周易》。根据民国期间著名易学家如高亨、李镜池等先生的观点,先秦应该还有其他筮书。因此,《易》之占筮从古到今一直是存在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左传》、《国语》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易》之占筮,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简单地排斥和否定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要正确地认识《易经》,我们必须以一种历史的理性的态度来面对它、研究它,最终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结论。
首先我们回归到先秦,回归到孔子,来看一下先师孔子对《易经》之态度。一般学者认为,孔子排斥卜筮,只言义理,例如《论语》中: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对于以上这句话,现代诸多学者认为是孔子对《易》的一种态度,即不提倡占筮,认为有德行即可,对易经占筮持排斥态度。
参《论语集解》:孔曰:“南人,南国之人。”郑曰:“言巫医不能治无恒之人。”包曰:“善南人之言也。”孔曰:“此《易•恒卦》之辞,言德无常则羞辱承之。”郑曰:“《易》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
《论语集注》:南人,南国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医,所以寄死生。故虽贱役,而犹不可以无常,孔子称其言而善之。此易恒卦九三爻辞。承,进也。复加“子曰”,以别易文也,其义未详。杨氏曰:“君子于易苟玩其占,则知无常之取羞矣。其为无常也,盖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由此来看,《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之注解相近,但皆没有对孔子占筮持排斥态度。从《论语集解》郑玄的“《易》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以及《论语集注》杨氏“君子于易苟玩其占,则知无常之取羞矣。其为无常也,盖亦不占而已矣”来看,他们甚至是肯定《易》之占筮,认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通过占筮可以得出的结论。无独有偶,在《礼记·缁衣》篇,我们也看到一句相似的话: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
由此来看的话,孔子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孔子习《易》之后说的,否则后面就不会引用《易》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了。通过上面这句话,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孔子这句话的用意是在于强调为德有恒的重要性,但是这里我们也丝毫看不出孔子排斥占筮的态度。而且,孔子在这里所引用的南国之人的话,认为人如果没有恒德,则是连卜筮也是不能做的,并怀疑这是古代的遗言。他进而发挥道,龟卜占筮都不能知晓,更何况是人了。在这里他明显是认为卜筮之灵应是高于一般人之知,后面他又用《诗》、《尚书·兑命》以及《易》之恒卦九三爻辞来论证此理。如果我们认为《礼记·缁衣》是汉人所编纂,掺杂入汉人之思想的话,我们可以在郭店楚简的《缁衣》篇找到对应的话:
二十三 子曰:宋人①有言曰:人而亡恒,不可为卜筮也 ②。其古之遗言与③。龟筮犹弗④ 知,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告我犹。”⑤
二十有三。 ⑥
①“宋人”,今本作“南人”。宋人,指周代宋国人。宋国,周初都商丘(今河南商丘),战国初迁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在鲁国之南,所以称“南人”。“南人”即简本中的“宋人”。
②“亡”,今本作“无”。“不可”,今本作“不可以”。“亡恒”,即“无恒”,无恒心。“卜筮”,古时预测吉凶,用龟甲称卜,用蓍草称筮,合称卜筮。《论语·子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③“其古之遗言与”,今本作“古之遗言与”。
④“弗”,今本作“不能”。
⑤“不告我犹”今本作“不我告犹”。“《诗》云”引文以后,还有“《兑命》曰”与“《易》曰”引文,简本无。刘信芳曰:竹简《缁衣》通篇不引《易》,疑此段文字乃汉儒添加。“《诗》云”引文见《诗·小雅·小旻》,“犹”,计谋,谋划。
⑥“二十有三”为简本全文章数。
释:该章为今本第二十四章。孔子说:宋国人有言说:人如果无恒心,那么就不可以做卜筮。那不会是古代人遗留之言罢。龟甲和蓍草尚不能知,更何况人呢。《诗经》上说:“我的龟甲已经厌倦,不告诉我该如何谋划。”
郭店简《缁衣》是现在学界著名学者如李学勤、廖名春等公认的子思的作品,且郭店楚简埋葬时间大约是战国中晚期,则该书成书时间还应上移。经过对照,我们可以看到《论语》、《礼记·缁衣》和郭店简《缁衣》所重的是前半部分,即南人(郭店简所言为宋人)所说的话。至于所不同的是,《论语》有恒卦九三爻辞,《礼记·缁衣》多出引《诗》、《书》的话,郭店简《缁衣》则只有引《诗》而已。通过对照,我们便可以看出《论语》中的这段话在郭店简《缁衣》及《礼记·缁衣》中的发展和演变。而且,通过对照,我们还可以坚持孔子说此话时的确是学过《易》的,而且对占筮并非持决然的排斥态度。但是,孔子所言之占筮与现代市场上的“算卦”、“算命”又有什么不同呢?
通过现代出土的简帛史料例如长沙马王堆帛书《要》篇等,我们对此可以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
马王堆帛书《要》篇云: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孔子老而好《易》,这一点再次得到了论证。当然,这里的所谓论证,更多是从孔子学《易》之时间来说的,是对上面我们所总结的孔子学《易》时间应在晚年的一个补充说明。
其次,孔子学《易》之目的,是以祝卜为后,是为了观其德义。是幽赞天地造化而达乎数,明其数而达乎德,又以仁守之而义行之。他特别指出了自己与巫史之卜筮的区别:“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也就是说,巫能幽赞天地造化但不能达乎数,史呢可以达乎数却不能达乎德义。对于史巫的卜筮,(我)接近了但却未能如他们那样,爱好它却并非如他们一样。孔子不无感慨地说,后世之士怀疑我的人,或许是因为《易》吧。其实我不过是以此求其德义而已,我跟那些史巫其实是道路相同而归宿不同。君子是以其德行求福,所以虽祭祀而寡少;行仁义以求吉利,所以虽卜筮而稀少。祝巫卜筮应该是靠后吧?
廖名春先生亦评价曰:
“百占而七十当”,说明孔子占筮并不只偶尔为之。《孔子家语·好生》说:“孔子常自筮”,并不是不涉古筮。所谓“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君子不能因为重德行而废祭祀,也不能因重仁义而绝卜筮,只不过是寡、希而已。因为“幽赞”才能“达乎数”,“明数”才能“达乎德”。不明占筮,不懂象数,是不能通晓《周易》的义理的。通过《周易》的占筮形式去把握《周易》的德义,这就是孔子虽力主“不占”但又未能摈弃占筮的原因。宋儒朱熹决非江湖术士,其《周易本义》针对王注、程传而强调“《易》本卜筮之书”,其用意或许也与孔子倡“不占”之教而又不废卜筮近。所以,我们不能执着于《论语》的片言只语,将孔子丰富、辨证的易学观简化为“不占”之教。
孔子于《易》,重在“观其德义”,“求其德”,也就是“不安其用而乐其辞”。《论语》“不占”之教只揭示了孔子不安其卜筮之用的一面,而孔子好《易》、欣赏恒卦九三爻辞,主要还在“乐其辞”而“求其德”。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获知,孔子的性命天道思想是与孔子习《易》分不开的。《论语》中孔子“罕言性命天道”是与孔子习《易》时间甚晚密切相关的。由于孔子习《易》以至好《易》的时间甚晚,据朱子分析可能近七十岁,所以诸弟子们很少听到孔子关于“性命天道”的论述(当然,这与孔子因材施教的理念也不无关系)。如果孔子习易在晚年得以成立的话,那么《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又“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等等,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认识。而结合《论语》、《礼记·缁衣》、郭店简《缁衣》、马王堆帛书《要》篇等,我们可以知晓,孔子其实并不排斥占筮,甚至在晚年经常占筮的。《易传·系辞上》言:
是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主子将以有为也,将以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於此。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马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致变,其孰能与於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致神,其孰能与於此。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我们会看到,《易传·系辞上》这段话与孔子对占筮的态度是不矛盾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是对孔子之言行思想的正确记述和理解。但孔子是将自己的占筮与当时巫史的占筮截然分开的。他认为自己虽然也占筮,这与巫史是一样的,但巫只是幽赞天地之化却不明数,史明数但却不知德义。而他自己呢,则是同过占筮不仅仅幽赞天地之化和明数,而且是通晓其德义的。而且,孔子是将德义放在最前,而将占筮放在后面的,占筮之目的,亦在于观德义之不爽。这就与同时代的所谓巫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样一来,我们便可明白,孔子之占筮与现代市场上所谓“算卦”、“算命”亦是根本不同的。
常会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本文刊载于王中江、李存山主编《中国儒学》,2013年12月。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撰:《史记》,卢苇张赞煦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
2、【魏】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1999年12月
3、【宋】朱熹注:《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10月
4、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3月
5、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187页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184页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320页
关于孔子性命天道的思想参笔者的博士论文《<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第三章第一节“对知天命之不同理解”。
参看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1.15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