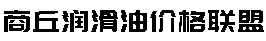![]()
对于我们八零后的童鞋们最不陌生的莫过于吃大桌了,有次和伙伴聊天,竟然来一句“我最好吃坐桌掉下来的下渣子菜了,酸类甜类,香类辣类,啥味都有,吃不够”。原来都好吃这一口,爽朗的笑声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打消了久违重逢的尴尬,也把我带到了童年的坐桌时光……
十岁之前我吃的桌特别多,这不得不归功于我老家家族人丁兴旺。先说我爸爸的爷爷弟兄六个,接着分支下来的爷爷辈我也数不清,我爷爷弟兄两个,但我有四个姑奶奶,我爸爸弟兄六个,我叔堂叔结婚我做迎接客(接新媳妇),添小孩待喜客这都要坐桌。
我六岁之前家里很穷的。妈妈最怕哪个叔又结婚了又添小孩了,这都要跟人家随礼送糖的。那时的十块钱是妈妈卖个养的小公鸡呀,鸡下的蛋呀,积攒了好几个月也不舍得花换来的呀。反正那时候能换钱的是绝不能吃的。换的钱可以买盐呀醋呀我上学用的学习用品呀,这些有了着落,妈妈也就不愁了,但要是遇到给人随礼妈妈就又该发愁了。
我们小孩儿哪管这些,只期待着那天好吃好喝好玩了。从叔结婚的头几天,我们姐弟仨人就该掰着指头数日子了,还念叨着桌上的吃食儿。
在老家睢县偏东南的白楼,坐桌还是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这也就是所谓的“五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吧。
![]()
过了十二点新郎新娘磕头行礼后,一般到一点左右开始发桌。
四个高高的长条板凳摆放在大方桌四侧,每桌八个人,小孩儿不上桌,跟着自己的大人在边上站着,那时主家是为了省钱,能省一桌是一桌,能挤一人算一人。
等我们小将们迫不及待地拿着筷子勺子在边敲边吆喝说饿时,八个凉菜已开始上来了。四荤四素,桌上稍微好点的会有牛肉羊肉,主家要是穷的话就用杂碎(猪耳朵,猪肠等)代替。对于我们一年见不得几次荤腥的熊孩子是用不了几分钟便一扫而光的。
![]()
接下来是八个热炒菜。炒菜都配瘦肉,但几乎都是肉少配菜多。然后是蒸碗。
老家的蒸碗是最有特色的,我不得不提一下。蒸碗分甜咸两种,最早以甜为主,原因还是穷,后来咸逐渐增多。我偏爱甜食,对坐桌的蒸碗甜食记忆也最为深刻。有炸好的红薯丸子,甜藕,山药,荸荠,蒸米等。因为是地锅烧制,木蒸笼蒸了大半天的缘故,所以上面撒了白糖的它们甜而不腻,百吃不厌。咸的蒸碗有排骨,肉丸子,炸小鱼儿,小酥肉,这些都是后来条件好陆续加上去的。每一桌每一家都大同小异。但最后都会有一碗红碗儿(红烧肉)收场。蒸碗告一段落后,便是孩子最期待的拔丝馍了。
拔丝馍应属睢县的特色,这一道菜至今是孩子大人最期待最挂牵的食物了。要说为啥恁稀罕它我还真说不清,是因为它是现做的现拔的,还是因为当时吃不完,怕烫嘴,找个纸盒可以包一点带回家,还是那一盘热气腾腾地拔丝馍放桌上,众人开始手忙脚乱筷子勺子齐上阵,越急越拔不掉,越急越想搁到嘴里尝一下的那种欲罢不能呢?
我是熊孩子当中最幸运的,因为拔丝馍的师傅是俺爹,每次都是现看先吃还带拿。
![]()
别看拔丝馍是很普通的菜,但它却是极考验师傅的功力的。一般都是由大爷爷门下的大徒弟也就是俺爹来完成的。馍切成手指大小的方块儿,在水里泡,沥好水后过油炸之晾凉放至一边。五六斤白糖(按照一盘拔丝馍用三两白糖的比例,一次是十五桌左右)在油锅里用勺子来回不停翻腾熬制(加少许油以防干锅),这时围锅站着的我们早已迫不及待了,眼巴巴地瞅着俺爹像变魔术似的转勺与转锅,俺爹嘴里大声喝斥道:“lie(站)一边去,热,别测到脸上去”。我们唯恐吃不上,又好奇白糖怎么裹住馍的,所以根本不听劝告,就算挨吵也不愿离开。白糖完全熔化成糖水,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步,白糖的稀稠跟火候时间经验有直接关系,如果熬过了时间,那做出来的就苦,如果不到时间,拔出来的馍又没丝儿,粘合不到一块。火候时间一到,刚炸好的焦馍要迅速放在完全熔化了的糖稀里搅拌均匀,糖稀完全裏住炸好的馍。这时,端盘子的已在一边等候了。装盘更要迅速,如果不迅速,十几盘的拔丝馍盛不到盘子便凝固成一团了。
盘子还没端上桌,又一轮疯抢模式已经拉开序幕。大人小孩的筷子齐上阵,有的小孩儿不知冷热,不自觉便把手伸了上去,猛一缩,赶紧放在嘴边吹一下,哈哈,被烫到了。就算用筷子夹住了也不敢直接放嘴里,要放一边晾凉才可以。咬上一口,外焦,香,甜,里软,面,还是甜,这时的糖已完完全全熔进馍里了。
一份拔丝馍搞定完,熊孩子便一抹嘴各自跑路了,根本不喝那碗酸辣鸡蛋汤的。
等我们长大等我们去了更多的地方,等我们品尝了更多的美食,才知道那大杂院里的大杂烩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可我们总是心心念着。食物一旦与记忆掺连,便多了它另外的味道。我们想念的不是仅仅是食物,还有对时光的感慨和对家人的挂牵……
END
往期精品回顾:
杨静丨豫东平原的二十四拜
杨静丨商丘睢县的烧饼加肉
杨静丨薄情世界温情待
杨静丨归家记:“麦茬儿黄,去瞧娘”
![]()
作者简介:
![]()
杨静,笔名:薇薇安。爱好一切与美好有关的文字。
![]()